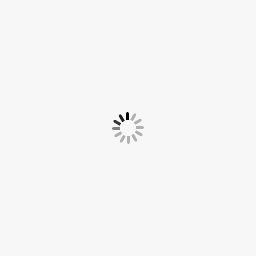鄭阿玉
圖片授權聲明

展品描述
採訪日期:2019年01月16日
受訪者:鄭阿玉
族群:阿美族
採訪者:楊富民、石竣旻
採訪地點:受訪者自宅
本篇受訪者為鄭阿玉,為七腳川系(Cikasuan)阿美族之後人,原居住在壽豐鄉光榮部落。父親曾為頭目,現任光榮部落之頭目為她的弟弟。鄭阿玉的故事可以看見原住民族群過去在日本時代的教育過程,以及對於日本文化的學習。其同時經歷過二戰時期美軍轟炸台灣的經歷,曾親眼目睹寿工廠(過去慣稱壽豐糖廠)被美軍炸毀。年輕時也曾經歷過豐田玉的熱潮,曾加入過豐田玉的產業之中。
「ひよひよひよこ、ちいさなひよこ(小雞小雞小小雞,小小的小雞啊)……」每當我唱著這首小雞童謠,總會讓我憶起那些甘苦交織的往事……。
1935年(昭和10年)我出生在寿番社(現花蓮縣壽豐鄉光榮部落),爸爸告訴我,祖先們剛遷徙至光榮部落時,那裡還只是一片荒地,到處都布滿粗壯的茄苳樹,粗得要三個人雙手張開才能圍住,開墾過程十分艱辛。爸爸他一共替我起了三個名字。第一個是我的阿美族族名—Panay,是阿美族語「稻穗」之意。第二個,是我的日文名字—糸静子,糸有「絲線」之意。國民政府來臺後,原住民族依照規定必須取漢人的名字。於是,我又有了一個新的名字—鄭阿玉。
我爸爸是部落的頭目,負責主持部落事務與通譯的工作,與日本人之間的關係相當好。然而,身為頭目女兒的我,生活卻不若童話故事中的公主般夢幻。那個時代部落生活十分艱苦,吃的食物千篇一律是番薯加上附近摘採的野菜,幾乎沒有肉食,這樣粗陋的食物即便吃到已經感到很膩很厭煩,為了填飽肚子還是得吃下去。住的是簡陋的茅草屋,中間僅僅用幾塊大石頭圍著一根木材當作支撐整間屋子的梁柱。每到夏天,都得擔心這樣脆弱的結構是否抵擋得住接踵而來的颱風。由於長輩沒有儲蓄的觀念,賺來的錢財常常是左手進右手出,沒有多餘的支出替我們添購衣物。因此,我們只能穿著自製的簡單衣物,夏天的時候雖然涼爽,但住在蚊蟲肆虐的山區,總會害怕是不是會感染上瘧疾;冬天更不用說,單薄的衣物抵擋不住寒冬侵襲,夜晚總得圍在火堆旁,邊睡邊打著哆嗦。因為沒有鞋子穿,腳上疊著厚厚的繭,有時候踩到尖銳的物品,血就流了滿地。
8歲那年,某天晚上,我正哄著哭鬧的弟弟妹妹,爸爸突然把我叫過去,對我說「Panay,明天妳就要去上學了。」我開心極了!興奮地幾乎睡不著覺。隔天早晨,我拎著風呂敷(日式包袱布)走到校門口,看見門口寫著「寿国民学校」五個大字,接著衝進學校裡面。我記得那時候念的是「花組」,班上除了原住民之外也有其他漢人的同學,但清一色都是女生。老師在台上所教授的內容,我早已忘了,但只要待在教室,我就不用幫忙那些累人的家務事,不用照顧年幼的弟弟妹妹,教室成為我苦難生活的避風灣。
上學那陣子,頻繁的空襲讓學校生活總是斷斷續續。說起空襲,用恐怖來形容已經算是好的了。有次空襲,整片天空響起嚇人的空襲警報,轟隆隆的螺旋槳聲一會就從天際傳來,老師用大得能蓋著警報的聲音對我們吼著:「集合!集合!準備回家了!」。我們像訓練有素的軍隊一般整好隊伍,隨著老師離開校園。步出學校沒多久,頭上呼嘯而過一臺轟炸機,老師趕緊要我們躲進田邊的渠溝中,我伏身蹲著卻沒注意到包著便當的風呂敷已大半浸泡在水中;不巧,剛剛那架飛機從山邊折返回來,往寿工場(指壽豐糖廠)投了幾枚炸彈,頓時火光四射煙霧瀰漫。年紀還小的我,沒管老師叫我們躲起來,嚇得爬出水溝逃命,卻發現浸濕的風呂敷根本提不起來,但為了活命我才顧不了甚麼便當,直接把便當往旁邊扔,爬出水溝邊哭邊叫著媽媽就這樣跑回家去。所幸當時空襲大多只攻擊公共設施,沒聽說過有甚麼人因為空襲而出意外。但我們寿工場就這樣沒了,之後他們把寿工場殘存的零件跟設備送到大和工場(今日光復糖廠),我們的甘蔗也得都送到那裡去製糖。
空襲斷斷續續持續一年左右,這段期間來了一群意外的訪客,一群以總幹事(村長)為首的日本人。他們擔心自己在糖廠附近的宿舍,會成為空襲的下一個目標,便借住到部落這來。於是,我多了一群日本人的朋友,與他們朝夕相處,雖然上課的日子少,但是日文卻越來越會說。戰後,日本人陸續遣返回國,有個熟識的朋友臨走前,拿了兩捆軍綠色綁腿布來到我家,想作為紀念品與我交換,看著他手中的綁腿布我苦惱著,家中實在沒甚麼值錢的東西。突然我靈機一動,請他稍等我一下,轉身就往山邊衝去,回來時我將滿把的過貓塞到他懷裡,對著他說:「這東西不成敬意,但還請你收下。」他抱著沾滿泥土的過貓笑著說:「不會不會,我很喜歡,妳要保重喔!」「你也是,再見了。」我拿著綁腿布揮著手與他道別。
隨著戰爭的結束,我離開了學校,回到家中開始學習如何務農,學習怎麼放牛吃草。我與牛發展出像朋友般親密的關係,不論刮風下雨,每天騎在牠身上,領著牠到處吃草。某天,部落來了一群大學生,爸爸說他們是地質探勘隊,每次看到我,他們都會跑過來跟我聊天,我聽不大懂他們說的話,但每次他們笑,我也會不自覺地跟著他們笑,他們還替我拍了好多照片,我都還好好地保存在鐵盒裡。但後來我才知道,這一群大學生們後來為豐田玉正名,讓豐田在之後經歷了一段繁榮的採玉時光。
我的丈夫大我兩歲,是同個部落的青梅竹馬。結婚那天,沒有甚麼華麗的結婚典禮,男方家屬來到家中,大家圍著火堆舉著酒杯喝著酒聊著天,一杯米酒傳過下一個人;有人拿著相機,讓我們兩個穿上傳統的服飾拍照我們倆就成了生死與共的生命伴侶。先生當完兵後,進入農會做精米的工作,完成精米程序的稻米,裝袋後一包足足有百公斤重,是相當累人的粗活。由於先生工作地點離部落實在有段距離,我們決定搬遷到豐田展開我們的新生活,記得剛搬過來的時候,這附近還只有五六戶人家而已。
1970年代(民國60年),這一帶興起豐田玉熱,整個街道喧鬧興盛好不熱鬧,我也乘著這股熱潮,跟著朋友到山上採過玉。天還沒亮就得出發,還得在山中爬上爬下的,總覺得不太適合自己,去了兩三次就沒再答應朋友的邀約。那個年代電視尚未普及,戲院成為了人們主要的娛樂場所,因為附近戲院的老闆是我的朋友,總是免費招待我進場,因此我那時候幾乎每晚都往戲院跑,看了好多的電影。
丈夫精米的工作持續做了38年後從農會退休,退休後我們一起去了好多的國家,看了好多的風景名勝,拍了好多好多的合照。我把這些相片貼在房間的牆上、收在床頭旁的相簿裡,就像他還陪在我的身邊一樣,有時候晚上睡不著,我會把相簿拿起來翻閱,翻著翻著才漸漸有了睡意。
兩、三年前我生了一場大病,臉上長出嚴重的皮蛇,眼睛睜不太開也幾乎說不出話來,待在家中休養了好一陣子,痊癒後我整整瘦了六公斤,身體狀況沒有之前這麼好,不按時吃藥的話身體很容易感到不適,也不能像從前那樣想去哪就去哪,甚至連以前會唱的日文歌曲都忘了大半。
以前上學那段時間,最喜歡的就是音樂課了,我總是唱得最大聲最賣力,老師還會叫我上臺表演給大家看。「小雞小雞小小雞,小小的小雞啊(ひよひよひよこ、ちいさなひよこ)……」,我常常想起那個在臺上邊唱歌邊跳舞的時光,那些日子雖然好苦好苦,但只要站在臺上我便能忘掉這些煩憂,便能像一個真正的公主一樣發光發熱。
關鍵字
資料來源
國家文化記憶庫
原始連結
收藏展品